最新訊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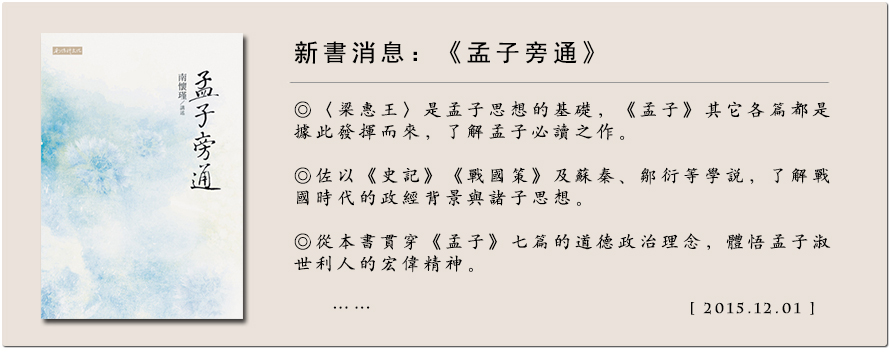
新書消息 《孟子旁通》
| 序言 生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,正當東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排盪撞擊的時代,從個人到家庭,自各階層的社會到國家,甚至全世界,都在內外不安、身心交瘁的狀態中,度過漫長的歲月。因此在進退失據的現實環境中,由觸覺而發生感想,由煩惱而退居反省,再自周遍尋思,周遍觀察,然後可知在時空對待中所產生的變異,只是現象的不同,而天地還是照舊的天地,人物還是照舊的人物,生存的原則並沒有變;所變的,只是生活的方式。比如在行路中而迷途,因為人為的方向而似有迷惑,其實,真際無方,本自不迷。如果逐物迷方,必然會千迴百疊,永遠在紛紜混亂中忙得團團而轉,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適從。
我是中國人,當然隨著這一時代東方的中國文化命運一樣,似乎是真的迷失了方向,也曾一度跟著人們向西方文化去摸索,幾乎忘了我是立足在本地方分上的一個生命,而自迷方向。《周易.序卦》說:「窮大者必失其居,故受之以旅。旅而無所容,故受之以巽。巽者,入也。入而後說之,故受之以兌。兌者,說也。」我們自己的文化,因幾千年來的窮大而一時失去了本分的立足點,因此而需要乞求外來的文明以自濟困溺,所謂「他山之石,可以攻錯。」這是勢所難免的事實。然而一旦自知久旅他方而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,那便須知機知時而反求諸己,喚醒國魂,洗心革面以求自立自強之道。正因為如此的心情,有些西方的朋友和學生們,都認為我是頑固的推崇東方文化的倔強分子,雖有許多歐美的友人們,屢加邀請旅外講學而始終懶得離開國門一步。其實,我自認為並無偏見,只是情有所鍾,安土重遷而已。同時,我也正在忠告西方的朋友們,應該各自反求諸己,重振西方哲學、宗教的固有精神文化,以濟助物質文明的不足,才是正理。
至於我個人的一生,早已算過八字命運──「生於憂患,死於憂患。」每常自己譬解,猶如古老中國文化中的一個白頭宮女,閒話古今,徒添許多囉嗦而已。有兩首古人的詩,恰好用作自我的寫照。第一首是唐人劉方平的宮詞:
朝日殘鶯伴妾啼 開簾只見草萋萋 庭前時有東風入 楊柳千條盡向西
詩中所寫是一隻飄殘零落的小黃鶯,一天到晚陪伴著一個孤單的白頭宮女,淒淒涼涼地自在悲啼,毫無目的地愴然獨立,恰如我自況的情景。偶爾開簾外望,眼前盡是萋迷芳草,一片茫然,有時忽然吹過一陣東風,卻見那些隨風飄蕩的千條楊柳,也都是任運流轉,向西飄去。第二首是唐末洞山良价禪師的詩偈:
淨洗濃粧為阿誰 子規聲裡勸人歸 百花落盡啼無盡 更向亂峰深處啼
這首詩也正好猶如我的現狀,長年累月抱殘守闕,濫竽充數,侈談中國文化,其實,學無所成,語無倫次,只是心懷故國,儼如泣血的杜鵑一樣,「百花落盡啼無盡,更向亂峰深處啼。」如此而已。每念及此,總是沓然自失,洒然自笑不已。
但是人生的旅程,往往有不期然而然的際遇,孟子曾經說過人有「不虞之譽,求全之毀。」一個人的一生,如果在你多方接觸社會各層面的經驗中,就會容易體會到孟老夫子的話,並非向壁虛構,確是歷練過來的至理名言。當在民國六十四年(西元一九七五年),我因應邀講完一部《論語》之後(事見《論語別裁》前言),由蔡策先生悉心記錄,復受社會各階層的偏愛,慫恿排版出書。但我自知所講的內容,既非正統的漢、唐、宋儒的學術思想,又非現代新儒家的理路,到底只是因應時代潮流的亂談,屬於旁門左道,不堪入流,因此便定名叫它《論語別裁》,以免混淆視聽,惑亂後學。
誰知出書以後,卻受到廣大讀者的愛好,接連出了十二版,實在彌增惶恐,生怕誤人。因為徒手殺人,罪不過抵死而已,如果以學問誤人,便是戕人慧命,萬死不足以辭其咎。此所以在我們固有文化的傳統中,學者有畢生不願著書,或者窮一生學力,只肯極其謹嚴地寫幾篇足以傳世的文章而已。這就是以往中國文化人的精誠,當然不如我們現代一樣,著作等身,妄自稱尊的作風。
但繼此以後,友人唐樹祥先生,在他擔任《青年戰士報》社長的時期,極力邀請在其報社繼續再講《孟子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等所謂「四書」之學。唐社長平時說話極為風趣,尤其對我更是暢所欲言,不拘形跡。當他擔任中正理工學院政戰部主任的時期,常來拉我去講課,而且勸說:在這個時期,大家都忙得沒有時間讀書,你寫書寫文章有什麼用?多來講課,教授青年學子,還比較有意義。總之,我在他的盛情不可卻的壓迫下,只好被他拖上講臺。但當他調任報社社長的時期,他便說:多講還不如多寫的好。希望我多寫點東西,好交他在報上披露。他的能言善道,我對他真是莫可奈何。
其實,我對講學則言不異眾,寫作則語不驚人,可以說一竅不通,毫無長處。但畢竟擋不住他的熱情,終於在民國六十五年(一九七六年)的秋天,開始在《青年戰士報》的樓上開講《孟子》。那個時候,也正是我思念在苦難中的父母,心情最難排遣的時期。講到孟子,就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千秋母教儀範的孟母,因此開章明義,便引用了黃仲則的詩:
搴帷拜母河梁去 白髮愁看淚眼枯 慘慘柴門風雪夜 此時有子不如無
當然,這種情懷,不只我一人是如此,在當時現場的聽眾們,大多數也有所同感。同時,蔡策也對講四書的記錄工作,極有興趣和決心,他一再強調,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。《孟子》講稿的因緣,就在唐、蔡兩位的鼓勵下完成。
後來因為俗務累積太多,自己沒有真正安靜的時間看記錄稿,因此,積壓多年無法完帙。目前,老古文化圖書公司的出書業務,正由陳世志同學來擔任。他站在現代青年的立場,又一再催迫出書,我常笑他猶如宗澤的三呼渡河,左季高的大喊兒郎們出擊一樣,壯氣如山,無奈太過冒昧!然而他畢竟強人所難地做了,還要催我寫序。事實上,《孟子》的序言,實在不好寫,因此只是先行略抒本書問世的始末因由,暫且交卷。書名「旁通」,卻又暗合宋代的桂瑛,及元代的杜瑛兩位先生所撰的佚書命題。但我所以定名「旁通」的本意,仍如《論語別裁》一樣,只是自認為旁門左道之說,大有別於正統儒家或儒家道學們的嚴謹學術著作而已,並非旁通各家學說的涵義。
南懷瑾 歲次甲子(一九八四年)六月四日端陽節 |
